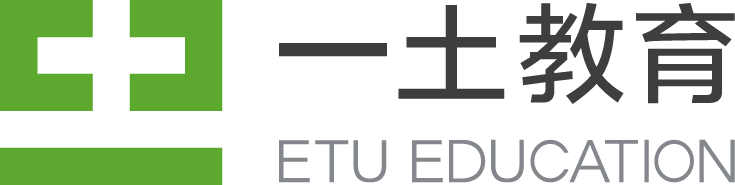本文来自《Vista看天下》 作者:毛晨钰

学校里,孩子们在这处位于北京三环的安贞西里新址上课不过5天,还没来得及在走廊两边展示区放上自己的作品。校门外,不少家长为了孩子上学方便也忙着又一次搬家。
他们不确定学校还会不会再搬,但“学校在哪儿,家就要搬到哪儿,我们要跟着一土和老师走”。
一土从最初诞生,似乎就伴随着这种“不确定”。
2016年初,准备从美国回中国的李一诺因为没给自家娃找到合适的学校,把心一横,跟先生申华章、朋友郭小月等联合创办了“一土学校”。
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,校长郭小月说,2016年4月下旬开始招生时,一土学校还在寻找校舍、办公室,第一个老师还没有到岗,就连面试家长都得不停换地方,“今天是胡同咖啡厅,明天是一个共享空间,后天有可能是某个家长办公室……”
考察一土时,厕所是她最在意的地方,她觉得一土的厕所没有异味。所以当爸爸李松蔚问她,以后在这里上学好不好?她点了点头。
当然,李松蔚把孩子送到一土来,并非因为他们的厕所。
李松蔚是一名心理咨询师,也在清华大学教书。当初应聘岗位时,他夹带了一个私心:女儿可以上配套的附属学校。
最终,朵朵却走进了开在老旧社区里的一土学校。这个决定让很多人不解。朵朵奶奶在微信上对李松蔚发起“质问五连”:你们大学的教师子女有几个会读这所学校?这所学校办了多少年?市重点还是区重点?学生平均成绩如何?毕业后都去哪里?

面试前,李松蔚曾专门去一土找了自己读研时的室友。这位室友在一土工作。在北京将台路的一个老居民区,李松蔚找到了传说中的一土学校。周围是没有电梯的六层老楼,穿过弯弯绕绕的居民区内小路,眼前突兀地出现一个小操场。操场不远处,还竖着一根砖红色大烟囱。李松蔚记得当时的一土“看起来非常不像一个正经学校”。
那位同学曾专门为了孩子上学,举全家之力买了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学区房。最终,他把孩子送到了一土。李松蔚相信,“他肯定认为这里对孩子更好”,出于对同学的信任,他也把女儿送到了这里。
后来,李松蔚专门写了一封给女儿的公开信,试图解释自己为什么给女儿选了一所“小学校”。里面提到了那个没有异味的厕所,有人泼冷水:也许只是因为在假期,所以厕所才干净。等到上了学,孩子就要面对这第一个代价了。李松蔚回复:这也可能是她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。
事实上,进入一土读书,要面临的问题更多,比如硬件受限。最初,一土学校借了北京80中的枣营校区,只拥有3间总面积120平方米的教室。
而这次搬家前,一土所有师生就在将台路一个居民区内上课。居民区住着不少老头老太,经常会抱怨孩子们吵得他们没法儿休息。为了与社区保持和谐的关系,学校、孩子和家长几乎全部出动解决问题。孩子们的画被印成台历,分发给这里的居民。台历上留了一个电话,如果居民觉得吵,可以打这个电话沟通。有当医生的家长,则为居民义诊。
一土似乎总是能把问题转化为自己的机会。2016年9月1日,一土学校第一次举办开学典礼。当时学校还在80中,为了避开原有初中的开学典礼,他们只得另外找地方。
一位老师出主意:能不能在故宫举行?结果,真的就去故宫了。
但到第三年,学生人数增长迅速,如果集体同时进故宫办开学典礼,那是不被允许的。学校决定按年级带学生进宫举办开学典礼,每个年级被分配了不同的研究项目,比如四年级专门研究故宫的排水系统,低年级的就可以做些跟颜色有关的研究。于是,一土的开学典礼就形成了一个传统:“六年走完一座宫殿”。这也恰好符合一土的项目制学习理念。
李松蔚的工作会跟来自各地的大学生接触,“有些学生只要看他们写的字,就知道他们来自河北衡水中学,他们的手写体几乎就是印刷体”。这群学生从高一入校就被要求每天练字以达到“标准化程度”,为的是能把高考作文的2分卷面分拿到手。
做心理咨询的李松蔚常常遇到有大学生问他,“我不喜欢我的专业怎么办?”在一些学生看来,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李松蔚却反问,“这怎么会是一个问题?”他觉得喜欢什么专业就去学什么专业,“你是一个三角形,为什么非要把自己削成一个圆呢?”
这归根到底就是一个“我是谁”的问题。在一节付费课上,李松蔚给出了这样的建议:“趁现在还有机会,好好培养孩子的心理品质,让他早一点去适应每个人都在思考‘我是谁’的未来社会。”

在今年的一土嘉年华上,“焦虑的家长”被频频提到。一谈到教育,家长似乎就忍不住开始“焦虑”。
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刘丹认为,“焦虑”从心理学上来说,“是对未来不确定状态的一种担忧”,这无关个人与社会对错,而是“人适应快速发展社会的一种反应”。落到教育上,就在于“未来前景不明,作为‘投资人’的家长不知道自己培养的孩子是否适合未来社会,就会非常焦虑”。
为了给孩子增加致胜砝码,家长只能要求孩子学更多学更快。
“你认为一个7岁孩子的数学能力是怎样的?”李松蔚自问自答道,自己女儿上学期刚刚学完20以内的加减法,“这是义务教育大纲对一个小学一年级孩子的要求”。
李松蔚说起有次一土老师在数学课上教学生折纸飞机。他们整整折了一个月的纸飞机。后来他问女儿,学校里最喜欢什么课。女儿回答“数学课”,因为折飞机很好玩。教识数时,老师又会用设置安全锥,让孩子们丢玩具数柱子的形式学会识数。李松蔚说:“他们会用比较好玩的形式去教学。”
不过比起女儿的幼儿园同学现在在小学学的,这似乎太简单了。他们现在学的数学是三位数乘以三位数。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,女儿假期要约一个朋友出来玩是非常困难的,“所有小朋友假期都在上补习班”。李松蔚觉得教育变成了一场“军备竞赛”,“你有一杆枪,我就得有一个炸弹,他就去搞一个导弹”。
李松蔚从小学霸,毕业于北大,是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中的胜利者。在他看来,现在很多家长的焦虑根源也来自这里:如何让孩子占有更多资源。他认为这种“焦虑”其实是一种“害怕”:“如果不把别人干下去,自己的孩子就会失去这个位置。”
郭小月说,这就是“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”。在互动中,学生的思考力会被调动起来,老师和学生教学相长,“必定会形成一个高效的课堂”。
曾有来访者看到学生在戏剧课上不听课,一个人拨弄椅子,老师们却仿佛“不在意”。来访者提醒郭小月:“为什么不管管呢?”郭小月回答:“为什么要管呢?”
课后,一土给学生安排了三十多门选修课,供他们自己挑选。有家长担心孩子太小没办法给自己选课,郭小月接受《中国青年报》采访时却说:“他选了啥不重要。不断选择中就会明白该如何选择。所以,他选择的这个行为才重要。”
但选择,也意味着要承担试错的成本。三年里,也有一些家长因焦虑而来,又因焦虑而走。他们觉得学校的教学进度如此之慢。郭小月承认,也有人会因为跟一土理念不合而离开,“但只是个位数”。

郭小月说,“学习都是有情感的。孩子如果没有情感,一定没有代入感,就没有那种动力去学习”。当一个学生喜欢某个科目的老师,在某个学科的课堂上感到自在,那么他就会很愿意学习这门课。
从一诞生,一土便备受关注。不过,每年15万的学费对很多家长来说是一个门槛。因此,在一些家长贴吧、社区,有人认为,一土说到底还是一种“精英教育”,是仅供极少数人享受的奢侈品,能把孩子送到一土的家长往往能承担更多的“试错成本”。
本刊记者与一位一土家长聊天时得知,他们一家三代为了就近上学,专门在原先一土所在地附近租了个200平米的房子。现在一土搬家,他们又得再次搬家,除了房租,还要支付2万违约金。李松蔚的太太也“稍微觉得有点可惜”,“之前花了很多心血和代价去为孩子铺路,现在就好像是重新开始计划一种新的生活”。
这是一所太“年轻”的学校,创校刚刚3年,要评价其教育理念的好坏,其实还太短。2017年,一位用户就在知乎上匿名发出提醒:“教育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事,才办了一年的一土,还至少需要5-10年的验证。”部分家长也依然保留着自己的“Plan B”,比如仍保留着“学区房”。
对认可一土的家长来说,似乎他们更看重的是教育的过程,而非5-10年的教育结果。李松蔚就不觉得一土是“精英教育”,他更乐意把一土叫做“常识教育”,“一个人只要接受正常教育就会成为一个正常的人”。
“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?”在采访中,本刊记者询问了每一个家长。
这群别人眼中的“中产阶级家长”给出的回答显得有些“标准过低”。有人说,“只希望他平安健康快乐”;李松蔚说,“希望她成为一个喜欢自己的人”;李一诺回答,“希望孩子全力以赴,成为最好的自己”。
时值下课时分,本刊记者在一土校门外遇到了接大儿子放学的方先生。他们为了孩子上一土,举家从福建福州搬到北京。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,他摊开手掌,郑重写下一撇一捺:“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成为一个人,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人,这是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能做到的。”